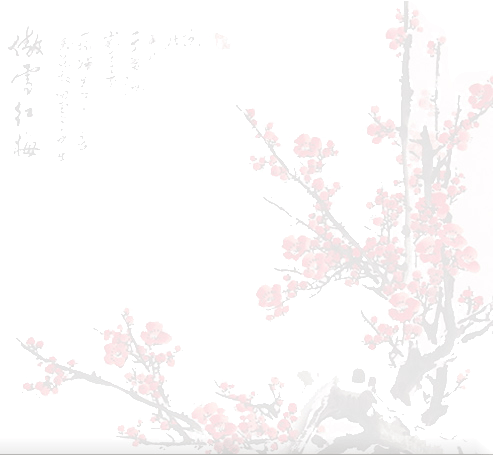5月19日下午,匆匆从深圳赶来上海的祖克曼,一下飞机就得到通知,原定当晚举行的音乐会,正碰上汶川大地震“全国哀悼日”。经过与主办方的紧急商量,祖克曼同意将上海音乐会延迟至周五,同时取消接下来两天在北京和沈阳的演出计划。幸好,这段时间祖克曼正处于休假中,所以并不影响国外演出的安排,否则恐怕他转身就得坐飞机“打道回府”了。
取消中国巡演的最后两站,根据演出合同中涉及“不可抗力”的条款,祖克曼将得不到任何赔偿,对他而言,这显然是个“坏消息”。不过对记者来说,倒因此多了与这位小提琴大师的接触时间。
面对灾难,音乐可以抚慰人心
闯进祖克曼所住的宾馆客房,里头居然高朋满座,虽然第三任妻子、大提琴家阿曼达·霍茜(Amanda Forsyth)撇下他自顾自出门逛街去了,但祖克曼并不寂寞。在芝加哥交响乐团中提琴首席张立国的陪同下,祖克曼正饶有兴趣地为一批新制小提琴试音,一边还即兴为记者拉了首小曲,并开玩笑地要在场者每人付100元门票费。
谈及地震灾害,祖克曼表示,他5月14日在澳门演出时获悉地震消息,第一时间便通过美国经纪人向中国灾区捐献了2000美元。然而,就像大多数被上帝宠坏的天才那样,祖克曼对他人的悲剧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同情,他一边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拨弄着小提琴琴弦,一边作惊人之语:“我看,不如让美国把打伊战的钱都捐给中国,要知道,那些枪炮弹药值几十亿呢,人类最大的支出就是花在制造灾难上了。”对于出生于以色列并在那里成长到14岁的祖克曼来说,人为的战争灾难给他的感触要远远多于“天灾”。
“面对灾难,音乐倒是可以抚慰人心的,如果可能的话,中国的音乐家们应该及时到地震现场,为灾民们演奏疗伤音乐。”祖克曼举例说,当年南斯拉夫被炸成一片废墟时,当地一个四重奏乐团就地演出,短短10分钟,让所有站在那里聆听的人暂时忘却了痛苦,仿佛时间停滞;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被刺后,街头也响起了塞缪尔·巴伯深沉的《弦乐柔板》。“我只是个音乐家、平民百姓,能做的微乎其微,我靠演奏音乐抚平人们的创伤,为生者,而非死者。”祖克曼表示,此次中国巡演,每场演出前,他都会带领全体观众集体默哀一分钟,并在致辞时表示将音乐献给灾民。
目中无人的“问题少年”
祖克曼的音乐成就令后人难以企及,他曾是“世界十大天才小提琴家”中最年轻的一位,灌录过上百张唱片,驰骋舞台长达40年,还兼具中提琴家、指挥家、教育家等多重身分,身上的头衔多得数不过来。与其面对面交谈,能感到一种强烈的“盛气凌人”。祖克曼几乎在所有的采访中都会说:“我最恨的就是庸才,各行各业都有庸才,庸才就像是这个世界的毒药。”谁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呢?大概只有目中无人的天造之才了吧。
听祖克曼描述自己的童年生活,倒是与球风“流氓”的斯诺克怪才奥沙利文有几分相像——事实上,小时候,他的书包里总是藏着一根斯诺克球杆。8岁时,曾学习竖笛、黑管与小提琴的祖克曼进入特拉维夫音乐学院专修小提琴,但他从小就是狂放不羁的“坏孩子”,几乎从来没在课堂上出现过,门门功课都不及格。每每逃学的他,总能在街头小混混的出没地点被逮到,这让家人和老师头痛不已。祖克曼调侃道:“如果你无法想象我曾经是个小流氓,那就请你看英国电影《逃学者》(Hooky),那就是我的生活。”为了守住这个“问题少年”,父亲还特地在祖克曼两年级时,为他请了家教,迫使其在家中学习,但据祖克曼自己说,这根本没用。
然而不久之后,所有“恶习”都可以忽略不计了。11岁时,祖克曼的惊人天赋被小提琴教父艾萨克·斯特恩(Isaac Stern)、大提琴泰斗帕布罗·卡萨尔斯(Pablo Casals)发掘,在这两位大师极力推荐下,祖克曼获得了海伦纳·鲁宾斯坦基金会的奖学金,赴纽约朱莉亚音乐学院,追随小提琴教学界的传奇人物伊万·加拉米安(Ivan Galamian)。加拉米安的三大嫡传弟子帕尔曼、祖克曼以及郑京和,均是莱文特里德音乐大赛(Leventritt Award)的金奖获得者,后来都成为声震国际乐坛的小提琴家。在旁人看来,能得到这样的老师指点,实属三生有幸,祖克曼却大笑着说:“即便是茱莉亚的课,我也没去听过几堂,对此,我感到十分骄傲!”
1968年至1969年,20岁出头的祖克曼代替生病的艾萨克·斯特恩登台,他的大名随即不径而走,声誉扶摇直上,在古典乐市场上,祖克曼一时间成为最受欢迎的小提琴家之一。同时,在室内乐方面,他与帕尔曼、巴伦鲍伊姆、阿什肯纳齐、杜普雷等一串“闪亮的名字”组成“黄金组合”,录制了许多经典专辑。虽然职业生涯中始终在与“高人”切磋技巧,但说起自己在小提琴上的成就,祖克曼自认还得归功于长年累月的“好学”:“要是不好学,怎么能听出别人的长处,取长补短呢?!”
在与张立国讨论琴弓拉奏技巧时,祖克曼根据自己最近在Youtube上看到的视频,模仿了一招海菲兹的专用技法。然而,当被问及是否主动上网搜寻海菲兹的资料时,祖克曼又表现得极为不屑:“我怎么会去找,是别人发给我的。海菲兹是‘小提琴皇帝’,千万别跟‘皇帝’学琴。”
采访中,祖克曼依然像一个骄纵过度的小孩。他一直在为新琴换弦、反复调音,手上一刻不停消,眼睛偶尔才抬一下。不过,据曾经采访过他的人说,这样的态度已属于“心情大好”了。传说中,祖克曼有诸多禁忌,一旦触及,老头便翻脸不认人,比如三段婚姻,尤其是为他生下两个歌手女儿的“发妻”Eugenia Zukerman——这位事业有成的长笛演奏家、小说家与前夫反目成仇,常常在媒体上恶言相加,称其毫无内心世界。幸好,尽管祖克曼常常用“我怎么知道”来搪塞记者的提问,但态度一直友好,不时冒出来的“冷笑话”也效果十足,惹得旁边笑声四起。
常常罢工的外交官先生
凭借着自己在小提琴界树立的声誉,祖克曼开始涉足指挥,他说:“我从16岁起就对指挥有兴趣,这不能算是转行,只能说是扩张。”祖克曼很快就征服了这个新的舞台。1979年至1981年间,祖克曼受邀出任英国伦敦南岸假日音乐节指挥;1980年至1987年,他接下圣保罗室内乐团音乐总监职务,并迅速让这个小乐团有了国际声誉;之后,祖克曼在巴尔的摩交响乐团任音乐节总监3年,又在达拉斯交响乐团主办的国际夏日音乐节担任了3年总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