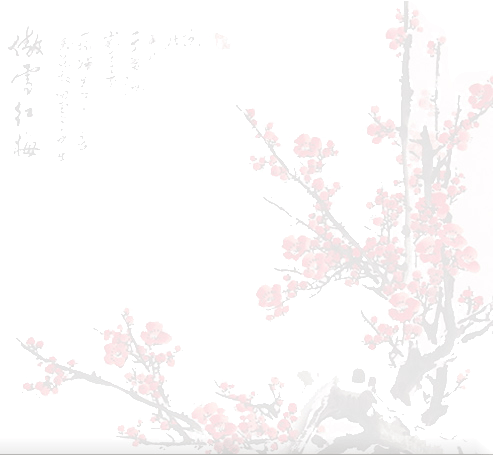我喜爱听音乐,尤其对二胡曲子有种特别的嗜好。周末的夜晚,一个人在书房里静坐,打开笔记本电脑,听上几首二胡曲,美妙的旋律犹如春风细雨荡涤天地间的尘埃,洗净一周工作劳累的倦意。可是,时常在此时,心灵的陶醉也伴着丝丝隐痛,因为如泣如诉的《江河水》仿佛也在诉说着久远的故乡月光下的那把二胡,那张国字型的英俊的脸,那段让乡亲们说起来令人心酸的往事。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在家乡的街上小学读书。那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,在有破烂的木窗框架而没有玻璃的教室里,音乐课老师教来教去的,也就是那么几首带有红色色彩的革命歌曲,像《东方红》,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。而在平日的生活里,大人们在生产队里劳动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家家所关心的是怎样设法填饱日日三餐的小孩子的肚子,有谁还会想到去听高雅的音乐呢?就是有人想听,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小集镇上,又可以到哪儿去寻求音乐呢?一个少年对音乐最高层次的理解,也就是扯开嗓子,放声高唱那几首旋律简单的歌曲了。
然而,一个夏日的夜晚,人们洗澡后都聚集在村东头公路上纳凉。月光普照,大人们或坐在凳子上,或躺在凉床上,闲聊着,说笑着。公路边有一口开阔的大水塘,清澈的水面上吹来阵阵微风,驱散着白天烈日余留下的炎热。我躺在凉床上,睡意渐渐袭来。就在这时,我隐隐听到夜空响起音乐声。静心细听,那音乐声从南方随风传来,时而大,时而小,时而悠扬,时而凄婉,是那么悦耳动听。此时的情绪瞬间兴奋起来,好奇心驱使我叫上邻居的小伙伴阿五,沿着公路向前循声探望。
走到村南头,音乐声越来越清晰。驻足南望,前面不远处的青石拱桥上,一群少年坐在石栏边的台阶上,一声不响地出神望着一个二十几岁的男青年。男青年坐在桥上,面对着桥下流淌的小河,正聚精会神地拉着二胡。他的左手指灵活如舞,在细弦上忽而上,忽而下,时而按着,时而揉着。他的右手不停地拉着,时而短弓音促,时而长弓音缓。他的额头气宇轩昂,时而浓眉紧蹙,乐声低沉哀怨,时而剑眉舒展,乐声高昂激愤。他若有所思,旁若无人,整个神情都沉醉在另一个音乐的世界里。这时的夜空明月高悬,皎洁的月光照着起伏的远山,照着清亮的河水,照着他那国字形的清秀的脸庞,也照着那浑厚而圆润的二胡声,宛如人的歌声,在静谧而广袤的夜空飞扬,飘荡。
我和阿五悄悄地走到小朋友中坐下听着。一曲拉完,街南头的小刚高兴地说:“保国哥,二胡太神奇了,你拉得真好听。你拉的叫什么呀?”
“《江河水》。”保国哥微笑地说。接着,他给我们讲述《江河水》的故事。( 文章阅读网:www.sanwen.net )
过去,东北有一对恩爱夫妻,丈夫服劳役离乡而去,因遭百般虐待,惨死异乡。妻子闻讯,如雷轰顶,来到当年与丈夫依依惜别的江边。面对滔滔江水,回忆往事,悲愤欲绝,诉之泣之,遥相祭奠。
“难怪听了我们想流泪呢。”小伙伴们说。“保国哥,再拉一首吧。”
就这样,在那个夏季,我时常和小伙伴们在夜晚跑到大桥上,在娇美的月光下听意境深远的《二泉映月》,思绪如潮的《三门峡畅想曲》,宏伟壮丽的《长城随想》,奔腾激昂的《奔马》,幽静空灵的《空山鸟语》……保国哥手中那把紫红色的光润而正直的二胡拉响了奇妙的音乐,让儿时枯燥的心灵领略了音乐的魅力,享受着乡村夜晚难得的一份高雅的乐趣。
第二年夏天的夜晚,我和小伙伴们依然跑到桥上,听月光下的二胡曲。就在这时,我们发现保国哥的身旁坐着一位特别的听众,一位大姐姐。她身着一件洁白的短袖衫,胸前拖着一根乌黑的长辫子。修长的腰,白净端庄的长圆脸,水汪汪的大眼睛,使我们想到小河边那池塘里的婷婷玉立的荷花。她轻轻地摇着一把纸扇,不时地望着保国哥拉着二胡,眼神里流露着难以掩饰的甜蜜的柔情,犹如那摇曳的荷花,醉心于美丽月光下的凉爽的微风。保国哥穿着蓝背心,拉二胡运动的双臂和双肩一块一块地肌肉突出,大姐姐柔美的气质更映衬了保国哥那坚实而强健的阳刚之美。
在深夜回家的路上,保国哥邻居的小波神秘地告诉我们,那大姐姐是保国哥的对象,和我们一样喜欢听保国哥拉二胡呢。
到了秋天。有一天,街坊邻居传说着一个大新闻:保国哥要去城市当舞台演员了。原来,一个大城市的文工团来我们公社招收舞台演员,一整天面试下来,只有保国哥的二胡演技脱颖而出。晚上,大队民兵营长对街坊四邻高声地说,当保国哥拉了第一首二胡曲《奔马》之后,三个评委就惊喜得睁大了眼睛。他们接着让保国哥一连拉了五首二胡曲,那个留着长发的男评委兴奋得连连点头,啧啧赞叹:“有潜质,有潜质。想不到一个多月来,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棵好苗子。”
这消息对保国哥的家人来说,无疑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特大喜讯。而我们街上的小伙伴听了这消息,既为保国哥满怀高兴,也感到心里十分难过。如果保国哥去了大城市,他就可以过上每天吃肉的幸福日子,再也不要为吃饱犯愁了。可是,如果保国哥真的去了,我们到哪儿去听月光下的二胡曲呢?
几天后,街上又传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:保国哥参加招收演员的政审表被退回来了。听大人们说,保国哥原来在省城的亲戚家里生活,上高中,也就是在那时他跟音乐老师学练拉二胡的。一年前回乡务农,他在生产队劳动表现好,又是出身贫农,非常符合文工团招收演员的各方面条件。可是,天有不测风云,在政审中有人反映,保国哥和地主家庭出身的大姐姐正在谈恋爱,他的思想有严重的政治问题。文工团主任找来保国哥谈话,神情严肃地提出一个条件,只要和大姐姐分手,他们就招收他。
保国哥闭门躺在床上两天一夜,不吃不喝,也不听家人亲戚的轮番劝说。大姐姐也让人给他送来一封信,说为了他光明的前程,他俩分手吧。傍晚时分,他眼睛里带着血丝,最终作出了一个决定,起床写了封信,让人送给那个文工团主任。晚饭后,他带上那把紫红色的二胡来到大桥上,在朦胧的月光下反复地拉着《江河水》,《苦闷之讴》,《悲歌》,声调是那么哀伤,悲愤。
保国哥和大姐姐之间的爱情是一颗政治炸弹,炸毁了他进城当舞台演员的美好的梦想。听说他的父亲气得拿起一根木棍要打保国哥,说他是一头倔强的驴,也不吃不喝地在床上躺了两天。
二胡声在月光下的石桥上又在响起。我们小伙伴们虽然依然享受着快乐,但是,每个人的心里却为保国哥感到难过,每一张稚嫩的脸上都没有浮起一丝笑容。况且,让我们心里感到更加难过和悲伤的,是那把二胡声给保国哥带来的天大的灾难。
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,我们小伙伴们在有些凉意的月光下来到大桥上。可是,一直等到月上中天,也不见保国哥的身影。这时,小波气喘吁吁地跑来,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惊异的消息:保国哥被民兵持枪抓起来了。他担心地说,在上午的公社文艺表演大会上,保国哥按节目安排拉了一首旋律欢快的二胡曲《奔马》,他的精湛的二胡演技博得了台下乡亲们的阵阵喝彩。演出结束时,乡亲们不愿散去,连声高喊:“再拉一首二胡曲”。盛情难却,保国哥走上舞台,又拉一首二胡曲《江河水》。乡亲们正听得入神,突然,公社革委会主任跑上舞台,立刻威严地挥手制止了保国哥的演奏,并用粗哑的嗓子对台下的乡亲们气愤地说:“目前,全国形势一片大好,我们要去歌颂。赵保国拉的什么二胡曲,声音像女人在哭泣,他这是在明目张胆地向大好形势表示不满,我们要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。”乡亲们惊呆了,人群也躁动起来。有人不满地小声说:“你懂吗?这是艺术。”可是,革委会主任还是气势汹汹地命令民兵把保国哥押走了。
第二天晚上,月光暗淡,小波在大桥上对我们说,保国哥正被关在湖边的农场里受审,破旧而又孤独的草房子的门口有两个民兵持枪站着。
第三天晚上,小波在大桥上忧伤地说,他们要保国哥承认,他是别有用心地用哭声似的二胡曲来攻击无产阶级的大好形势。不然,他们就恶狠狠地用武装带抽打他,把家里人送来吃的山芋扔到波浪翻涌的湖水里。
第六天晚上,月色昏暗,小波在大桥上哽咽而悲伤地地告诉我们,遍体鳞伤的保国哥在草房子里自尽了。他们发现,桌子上放着让他写的检查,但检查纸上面只写着几个字:让我带上二胡上路。
保国哥这次真的上路了,他要去那永恒的天堂。天空阴霾,秋风萧瑟,山岗上飘落的枯叶伴着乡亲们的泪水,伴着大姐姐嘶哑的哭泣声,伴着亲人们粗旷而奔放的悲歌为保国哥送行。小伙伴们跑在送葬队伍的后面,泪眼中透着纯洁而又不解的目光:保国哥,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呢?
保国哥走了,带走了那把紫红色的正直的二胡,带走了月光下的美丽的二胡曲,带走了小伙伴们的欢乐;留下的,是石桥上凄凉的月光,是石桥上少年心灵的不尽的伤痛,是石桥下小河水流淌不息的凄然的思念声。
三十多年过去了。每每在二胡声中忆起那段月光下的往事,心中总是涌起难以抑制的憾意:保国哥是不该死的,他应当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时代,能够自由自在地用美丽的二胡音乐来陶冶人们的心灵;更何况,在任何一个时代,任何一个民族都离不开艺术的熏陶。